●作者/Christopher W. Lowe上校
●译者/VAN、硕宝他爸、硕宝他妈
●校对/Nangwa
●取材/Historical Case Studies of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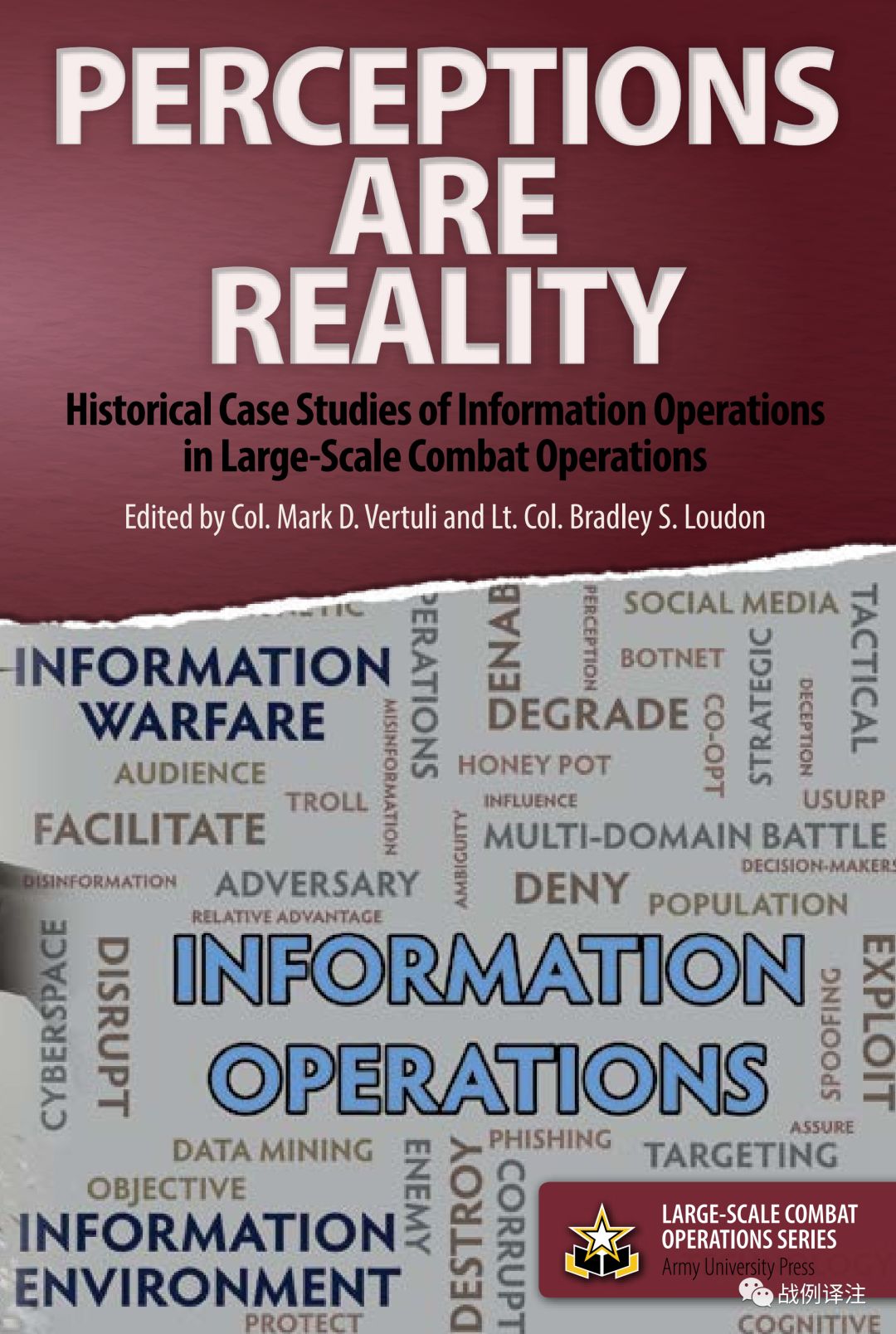
冷战后期,美国和苏联都发展了复杂学说,以应对在指挥和控制中对计算机、无线电、传感器和其他电子器材的依赖。苏联称之为无线电电子战,而被美国最终将之命名为信息作战,这些学说使得战场信息的流量和处理与后勤、火力和演习一样成为战争目标。导致这些学说发展的控制论逻辑——经过十多年非常规战争后,现在变得模糊了——应该再一次引起我们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思考。
信息战发展的源头,不是孙子或者克劳塞维茨,而是战争史上相对较近的产物:“电子战场”。1969年,时任陆军参谋长威廉·查尔斯·威斯特摩兰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了它的诞生:
在未来的战场上,通过数据链接、计算机辅助情报评估和自动火力控制的使用,敌军将几乎在瞬间被定位、跟踪和锁定。
随着第一轮打击概率的增大和监视设备可以持续追踪敌人,派遣大规模部队来锁定敌人的必要性将变得不那么重要。1无关政治的、枯燥无味的、没有错误的、没有摩擦的、没有庞大的军队和高伤病率,威斯特摩兰的战场被解读为在越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战场——一场完全不同的,更令人愉快的战争背景。
事实上,威斯特摩兰的构想在越南一直呈现着,它已经在战争期间的作战指挥上留下了印记。在每一阶段,有效的决策和部队控制都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和往往相互依赖的电子技术,来影响到包括无人值守的传感器、计算机和无线电通讯。
三年前,威斯特摩兰担任美国驻越南高级指挥官,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导开发了一套系统,以识别和阻止北越军队(NVA)沿着胡志明小道的行动。
这个项目在无人值守震动、化学和电磁传感器上花费了6.7亿美元,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麦克纳马拉线。传感器将数据传输给上空的飞机,飞机将这些信息转发给位于泰国那空拍侬府的一个行动中心。那里,原始的传感器数据被处理、显示、转换成目标数据,并提供给那些可以参战和摧毁敌人部队的攻击机。
地面部队迅速探查无人值守传感器的战术效用。1968年,麦克纳马拉线完工之前,北越军队袭击了附近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火力基地。威斯特摩兰将未安装的传感器转移到那儿,据一名官员称,此举可能使美国的伤亡人数减少了一半。此后不久,越南部队在道路网络和设施周围巧妙地部署了传感器。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MACV)也广泛依赖电脑进行情报分析。在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克里斯蒂安少将指挥下,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情报人员变成“一个计算机化、自动化的情报处理组织” ,一千多名美国和越南共和国情报人员审问、利用或分析敌方囚犯、武器、文件和其他材料。
这个“未来化的情报系统”包含了每一个被俘人员的数据库。同时,计算机系统在作战指挥方面的表现也令人期待。在1965年成立的美国陆军自动数据战场系统司令部的支持下,和驻德美国第七军一起对战术作战系统(TOS)进行了开发和战场试验。其开发人员计划使用TOS“通过一个在线的、接近实时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为陆军战地指挥官和其参谋提供相关和及时的情报、行动、火力支援协调特定的信息”。
在此期间,无线电通信的使用也激增。截止至1971年,标准陆军旅拥有539台电台设备。自1943年,每个旅的战地电台数量都有大幅度增长。朝鲜战争,师部有8个频道,而在越南有32个,增长了3倍。甚高频(VHF)无线电设备为较低战术层次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使部队能够在破坏性地形的视野范围外进行行动。
此外,驻越美军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享受“战术层面的语音加密”和内部通信的“全自动电话系统”。为了支持大规模的通信工作,师级层面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一名是无线电操作员。维修数据进一步凸显了拥有通信密集这一特征的美国战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通信部队为越南150个维修地点的通信设备提供了服务,在那里安装了50多万个通信零件。
威斯特摩兰将军本人最恰当的总结了语音通信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可靠的通信保障,是不可能认真考虑具体任务的作战计划。与此相比,那些没有通信的乌合之众的射击和机动是不可控制的。”在同一时期,苏联军队也在指挥和控制方面增加了对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的依赖。1964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通信系主任伊万·库尔诺索夫少将(Ivan Kurnosov)指出,“很难找到一种作战手段,其效能的发挥不依赖无线电电子设备。”
伏龙芝学院副院长VasilyGerasimovich Reznichenko中将评估认为,高机动性平台和可靠的通信结合将扩大、加速和加强作战行动。雷茨尼琴科认为,战争将是“具有广泛空间性、高活跃性和流动性,从一种战斗到另一种战斗快速改变”和“危机局势的加剧”。总的来说,苏联似乎理解电子战场带来的困境:尽管信息流在增加,但是指挥官“收集、处理和传达信息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上方法也许是增加战场控制节点的数量,从而缩小控制的范围。然而,正如一位苏联军官所指出的,鉴于军队的规模,“这将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这又反过来使得这些机构的管理工作被大大的复杂化”。换句话说,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试图让更多人进入这个循环中只不过是徒增复杂而已。
这种复杂性只有在计算机辅助系统的协助下才能被管理,该复杂性在苏联文字中被形容为“部队控制”问题。然而,与其他战场设备一样,通信和计算机网络也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和战斗摩擦的影响。这十分重要,因为它对指挥和控制本身而言构成了一个弱点。1963年一期《陆军》刊登了美国陆军查尔斯·J·戴维斯中校(Charles J. Davis)的一篇文章 “指挥控制与控制论”。他在文中准确的阐明了这一点,将现代指挥与控制描述为一个容易瘫痪和死亡的神经系统:描绘了战场上的这个“机器人”。它通过声音、光、电磁辐射和压力的微妙机制感知环境中的诸多情况。无数的感觉信号,以不同的重复频率被量化,沿着“附着神经纤维”的精细网络向下移动,到达反射中心,在那里,它们刺激第一反射弧。不足的处理,导致了该系统的肌肉效应智能指令的产生。
因此,“数据” 进入中央传输系统——脊髓和它的惊人通信主干——按自主方式进入主处理器,也就是大脑。这里,大量的信息按照一组有序的指令被分拣、关联、拒绝和处理。这些指令,如果你愿意,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神经发送到恰当的效应单元,如战场上战士的手、腿、胳膊、脚、眼睑和手指。有些时候,系统发生故障——内部疼痛、大脑或者中央神经系统的损伤,所有的反应将会停止。这时必须对其进行保护,否则它就会被毁坏。
为了全面理解类似“机器人”——戴维斯的意图和暗示,更好地理解“控制论”就显得很重要。其创始人将它描述为“通信和控制”的科学。根据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长经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从希腊词kubernetes或‘舵手’”中推究而来的控制论,“这个词与我们最终得出‘州长’这个词的希腊词相同”。维纳负责的战时关于通信和控制问题的挑战是防空技术的改进。近来年,航空技术已经赶超防空技术。
随着飞机飞行高度和速度性能的提高,这意味着空中卫士经常无法从视觉上获取和攻击从头顶飞过的敌方飞机。维纳采用了伺服系统或反馈回路系统的想法,设计了一种能够“根据飞机之前的轨迹信息预测飞行轨迹”的机器。维纳和他的同事们将继续着眼于伺服系统或反馈回路系统的想法,来作为智能机器的原型。
反馈回路是一个因果循环的过程,通过信息反馈调节“输出”。负(或自调节)反馈回路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恒温器。恒温器通过环境“感知”温度信息,来升高或降低热风或冷气的输出;一个新的温度读数结果将导致恒温器重新调整输出。反馈和反应的进程的触发是无限期的,只要恒温器持续“感受”环境(温度方面)和能够发送信息或者下达指令调节冷热。据维纳判断,恒温器的“行为”与人类个体体内平衡进程差别不大:[如果]我们的体温从正常体温98.6[度]上升或者下降1度,我们会注意它,如果上升或者下降10度,我们肯定会死。我们血液里的氧气、二氧化碳和盐,以及流经我们无管腺体的激素,都受到生理机制的调节。这个机制趋向于反抗任何一个背离它们层面的变化。这些机制构成了大家所知的体内平衡,是一种负反馈机制,该机制我们可以在机械自动装置中发现例子。
与同事阿图罗·罗森布鲁斯(ArturoRosenblueth)和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一起,维纳认为,负反馈系统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不论是人还是机器。控制论专家认为,所有负反馈系统的共同目标,包括机械自动装置和生物,是为了防止熵。然而,正如恒温器和体内平衡例子所展示的,控制论系统需要不间断的信息流来平衡熵。如果没有连续的信息流,控制论系统也许既不能适当地“感知”环境,也不能指挥新的行为。正如戴维斯所表述的以及約翰·博伊德上校稍后(和更著名)用定位、观察、决定、行动(OODA)循环所描述的,军队是不断感知和适应信息处理系统:“规定任务,情况评估,考虑多项行动方案,然后选择其中一项;发布命令;监视作战进展;随着时间推移调整命令。”
自适应(循环)周期的成功——和作战的结果,甚至战争本身—— 取决于军队通信系统保证信息流和避免熵的情况。“通过区域通信系统和复杂媒体传输网络以及交换中心进行进展反馈。利用控制信息和新的战场信息来开始新的周期——周而复始直到被对方击败或者双方力量达成协议。”
苏联人长期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待军队。正如斯拉瓦·葛罗维奇(Slava Gerovitch)所主张的,苏联思想家,如阿列克谢·李亚普诺夫(AlekseiLiapunov)——苏联最早期和最多产控制论支持者之一——认为“武器系统如同控制论系统,包括机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对于李亚普诺夫(Liapunov)来说,军事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其大脑是指挥官。正如俄罗斯专家和美国陆军高级军事研究学院副院长雅各布·基普所说,根据Irina Grekova,“应用高等数学主要专家之一,也是茹科夫斯基学院长期教授”, 早在1952年,苏联人就在讨论控制论,仅晚于维也纳出版物《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四年。
1953年,苏联新上任国防部副部长A.I.贝尔格海军上将负责开发苏联无线电子工业和控制论。到1958年,苏联将维纳的控制论翻译成俄语,一年后,“伏龙芝学院组建了军事控制论系。”
20世纪60年代,目睹了电子对抗(ECM)在越南和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成功用来对抗苏联装备,苏联开始整合各种方法来攻击战场对手的通信网络——也就是,采取具有决定性反击的指挥和控制理论。苏联将其命名为“radioelektonnayabor "ba”,即英语里的无线电电子战(REC)。
经过一段时间关于无线电电子战“propernature”的内部辩论后,苏联少将A.I.Paliy出版了《无线电电子战》,从而促进高层就这一理论达成了共识,其被David Chizum称为“苏联电子战元老”。根据指挥官(美国海军)Floyd D. Kennedy,一项1978年美国陆军研究将无线电电子战形容为联合“信号情报、电子侦测、密集干扰、欺骗和火力压制一起攻击敌方的组织和系统”。这种多元素的联合将“限制、延迟或者使敌人指挥和控制系统使用无效”,与此同时,对苏联系统进行保护。
无线电电子战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在集成方面所进行的强调,同时联合多个保护和破坏手段形成一个“大于其余各部门之和”的整体,以支持地面机动方案。美国理论及时适应无线电电子战的集成规则,这些规则一直保存到现在,成为信息战定义的特征。似乎,苏联复杂的无线电电子战理论算不上威胁,美国在原始战斗力方面远远超过他们。过去十年,苏联在军事装备的开支上,超过美国2,400亿美元。自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来,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赢得战争。
国防研究与工兵局副局长威廉·佩里的做法是,通过技术“优势”来“抵消军事装备数量的不足”。根据佩里的战略,国防部追求的“抵消”技术,包括“监视系统”、数据通信系统、“定位系统”和导弹“制导系统”——都以某种方式依赖着电磁频谱。在1975年到1978年之间,根据计划,美国国防部和空军进行了几项研究,加大了对电子通信技术的投资,无线电电子战理论就是利用的这一技术。这些努力最后成就了美国版的无线电电子战,被称为指挥、控制和通信对抗(C3CM),其也同样集成了电子战(EW)、作战安全(OPSEC)、军事欺骗(MILDEC)和物理毁坏。
与C3CM关联的直接挑战之一是共同条令的一致,在战争的潜在方面,确保战场空间上统一的和自我强化的C3CM活动。为应对这一挑战,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和空军战术空军司令部在1981年12月出版了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册子525-7《指挥、控制和通信对抗联合作战概念》。指挥、控制和通信对抗联合作战概念在部队使用了近十年,直到1991年5月被陆军野战手册90-24《指挥、控制和通信对抗多任务程序》所取代。C3CM概念首次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的运用,不是在欧洲的大草原,而是在科威特的沙漠中。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其邻国。随后发生的海湾战争证明了美国军队在过去十年的技术、条令和训练的复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并解放了那里的人民。一些人还称赞沙漠风暴为一种新型战争的概念。在这种战争中,信息和知识,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空军退役上校和信息战专家,阿兰·坎本在战后不久写到,“知识与武器和战术一样重要,相信这个概念主要通过指挥和控制手段的破坏和瓦解,使得敌人投降。”
事实上,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军用了大量的手段来破坏伊拉克指挥和控制,“充分联合软硬杀伤力量”。对雷达站、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中心、电力节点和通信中继的破坏和中断有效地切断了伊拉克的信息流。使得许多人用斩首、失明、瘫痪和震惊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美国攻击伊拉克军队的效果。例如,战争期间,科林·包威尔将军描述“作战计划”为“首先摧毁伊拉克防空系统和他们指挥、控制和通信网络,使敌人成为聋哑瞎。”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的战略是……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切断它,然后我们消灭它。”
1993年,一名空军中尉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高度集中化的伊拉克系统证明,C2系统易被空中力量所摧毁。苏联的装备与西方的学说混合在一起,对于萨达姆来说,他们首先是瞎的,然后是瘫痪的,最后被联军的大规模空袭所破坏”。
然而,不仅仅是美国主导的电磁频谱,还是物理摧毁或电子战,这些共同导致了伊拉克的瘫痪。
美国心理战(PSYOP)部队对伊拉克军队使用传单、扩音器和电台广播进行攻击,使得近87,000名伊拉克士兵投降。
大量伊拉克部队投降和逃亡无疑使得伊拉克指挥和控制(C2)瘫痪,剥夺伊拉克高级指挥部的“眼睛和耳朵,使得部队士气低落和战术反应能力下降。
即使美国的轰炸为敌人的投降提供了动机,但是,心理战的宣传也向伊拉克士兵提供了如何投降的指示。
海湾战争似乎验证了将军事力量视为依靠信息流进行指挥控制的控制论逻辑。作为一对未来主义者,Alvint和Heidi Toffler在他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战争和和平;生存在20世纪的黎明》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拉克军队,特别是在他们的雷达和监视被切断后,是一个传统的‘军事机器’...相比之下,盟军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内部反馈、沟通和自我调节能力强得多的系统。它就是,事实上,至少部分是...一个会‘思考的系统’。”
正如Alan Campen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领导的联盟取得了这种相对优势,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苏联——伊拉克的主要导师——是第一个让人相信,通过攻击对手的控制结构,可能会打破战争的平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的政治控制结构本身的解体,实际上是在美国领导下推翻伊拉克指挥结构的同时进行的。这两个事件,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期间的几乎完胜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将导致对威胁、机遇和意识形态的重大重新评估。
海湾战争之前,网络评估办公室(ONA)发出了一个评估声明,针对苏联长期坚持的一种说法,即一场军事技术革命正在导致“军事竞赛性质的重大转变”。这个评估报告,题为《军事技术革命:初步评估》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压倒性胜利”解读为革命实际上已经到来的证据。53然而,评估也强调,美国正处于“革命的开端”。54虽然美国拥有精确制导武器、信息和仿真系统等重要技术,但它只能利用“其战斗潜力的一小部分”。55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力,将最有用的信息迅速传递给最需要这些信息的人。”56
在介绍后来被用于军事理论的语言时,该报告声称,“信息优势很可能是未来冲突中有效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信息优势可能是未来冲突中决定性的行动”。57此外,该报告推测,由于交战双方也了解信息支配的决定性本质——尤其是在目睹了海湾战争之后——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现象。如果允许敌人在和平时期利用信息网络,会冒着敌人支配信息的风险,“这将迅速导致友军逐渐无力执行高度一体化、信息密集的军事行动,这对战争的成功至关重要。58从本质上说,如果美国不能继续保持信息的主导地位,它将失去其军事力量的威慑力和强制性。
该报告断言,在战争期间,美国很可能通过“全方位行动”取得信息优势。59“针对敌方地面信息网络的战略打击(包括所谓的‘电子打击’和特种作战部队打击),最好与空间控制作战同时进行。”60与苏联的无线电电子战(REC)和指挥、控制与通信对抗措施(C3CM)一样,主导地位来自于摧毁指挥和控制系统。
紧跟着海湾战争和网络评估办公室的军事技术革命的报告,托夫勒夫妇根据他们的早期著作《第三次浪潮》(ThirdWave)发展了他们颇具影响力的论点,并在《战争与反战争》(Warand Anti-War)中充分阐述了,“我们赚取财富的方式是我们制造战争的方式,我们反抗战争的方式必须映射我们制造争战的方式。”托夫勒夫妇认为,历史的特点是“波浪”,财富的产生和战争的发生都遵循特定的形式。
第一次浪潮——始于古代并主要结束于工业革命——这就是农耕时代。农耕时代的战争是季节性的、间歇性的、不专业的、技术上不成熟的战争。第二次浪潮是经济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生产、高致死率和机械化。第三次浪潮,只出现在《战争与反战争》时期,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和经济中的日益普及。托夫勒夫妇声称,“信息现在是破坏力的核心资源,就像它是生产力的核心资源一样。”
这篇论文为陆军看待ONA报告中所提出的军事技术革命提供了镜头。托夫勒夫妇在陆军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982年,托夫勒夫妇与一批有影响力的陆军军官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首长、指挥官多恩·斯塔里将军(Donn Starry)。63当时,Starry正在进行有关大规模作战的条令和教育改革,包括发展空降作战和建立高级军事研究院(SAMS),这两项后来都有助于解释军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托夫勒夫妇现在看见了海湾战争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开端之战: “1991年,中东的夜空和沙漠中发生了一件世界三百年未见的事情——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的到来,非常接近地反映了一种新的财富创造形式。”64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三次浪潮的影响,陆军直接转向托夫勒一家,邀请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College)的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题为“军事革命:21世纪的陆军”。65此外,正如陆军参谋长Gordon R. Sullivan将军所说的一样,他们借鉴了托夫勒在制定内部文件方面的见解,比如《信息时代的战争》(Warin the Information Age)。
《信息时代的战争》(War in the Information Age)支持托夫勒的观点,即知识——被陆军翻译为“信息”——正成为战争的中心资源。在此过程中,报告的作者重申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电子战场”和威廉·佩里的间接战略的基本逻辑——即,通过电子技术的集成而实现的更完善的信息收集和共享,将比规模更大的军队具有显著优势。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军事技术革命、军事事务革命、信息革命和第三次浪潮战争的讨论,美国国防部着手更新其现在备受尊崇和经受过战争考验的指挥、控制与通信对抗措施(C3CM)理论。在中间的十年中,联合参谋部发布联合作战出版物(JP)3 - 13.1,指挥控制战(C2W)联合条令,坚持声称“能够塑造敌人指挥官对战场情况的判断”,并使联合部队指挥官(JFC)”通过指挥与控制系统(C2)处理信息决策的周期速度比敌人指挥官快,”从而奠定联合部队的信息优势。67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对海湾战争中敌人的投降表现,以及对对手决策者致盲行动的贡献,指挥控制战(C2W)将心理战(PSYOP)添加到早期指挥、控制与通信对抗措施(C3CM)相关元素中,包括电子战(EW)、作战保密(OPSEC)、军事决策(MILDEC)和物理摧毁(PhysicalDestruction)。
然而,一种新的术语——信息作战——将很快取代联合指挥控制战(C2W)的基本作战原则。1995年8月,早在指挥控制战(C2W)发布前不到一年,陆军发布了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宣传册 525-69,定义信息作战。68为了与第三次浪潮和军事革命(第三次军事技术革命)(RMA) 话语相适应,信息作战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本小册子中,时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指挥官的威廉·哈特佐格将军宣称:“信息时代的模式将...改变战争的方式。”
撇开革命宣言不谈,信息作战概念既确认又程序化的认可了基于苏联无线电子战(REC)、指挥、控制与通信对抗措施(C3CM)和指挥控制战(C2W)的逻辑。在语言上,这听起来非常类似于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对电子战场的设想,信息作战的概念描述了数字化和电子通信的优势:“数字化还将通过精确的友好信号,抑或威胁的信号定义,以及更新武器系统识别软件程序,帮助作战识别和增强态势感知。全球通信网络和数字化战场之间的直接连接将使精确打击高价值目标成为可能。”70然而,同样被认可的“未来C2系统”的功能,“被认定是建立在我们行使电磁频谱优势或优越性的基础上的。”71
1996年8月,在引进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概念)一年后,也就是在JP 3-13.1之后的5个月,陆军出版了《战地手册》(FM) 100-6《信息作战》。根据这一概念,新的作战原则包括公共事务(PA)和民事事务(CA)作为补充的信息作战要素。正如早期将心理战(PSYOP)包括在指挥控制战(C2W)中一样,将公共事务(PA)添加到信息作战中似乎是早存在于海湾战争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教训之中,特别是关于不仅穿梭而且跨越于战场的信息流。这场战争证明了媒体的普遍性和力量,它们主要通过英语卫星新闻传播到全球的受众。该作战原则承认,这“可以极大地影响战略方向和军事行动的范围。”
同样,民事事务(CA)被认为对信息作战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在全球信息环境中与关键组织和个人进行沟通;例如,民事事务(CA)与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会等私人志愿者组织的传统关系。”73此外,民事事务(CA)与国际行动家和平民接触,意味着它可以保护和塑造国际、地方、公共通信环境中的信息流。
陆军部队将指望这种扩大的信息作战理论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维的行动期间,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中提供优势。然而,在这些行动中,在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所称的“人民内部战争”中作战的敌军,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深思熟虑的战略,以检验信息作战的基本控制论逻辑的适用性。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在所谓的“识别阈值”以下的小型分散网络中活动,使用的是低劣而非高端的技术,这使得破坏敌方作战指挥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不是难以忍受的。74与此同时,这些不对称的敌人对联合部队的指挥和控制几乎没有任何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在过去20年里,赢得“人心”一直是信息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足为奇的是,指挥官和信息作战的执行者严重依赖该原则最新要素的整合,每一个要素基本上都是一种公共传播手段: 心理战(PSYOP)、公众事务和民事事务。这几乎肯定默认重新解读了这一原则。那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非常规战争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尤其有可能从公共关系和战略沟通的角度理解信息作战,尽管该理论具有控制论的设计和明确的对手焦点。
当然,公共通信在现代作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未来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几乎肯定需要各级指挥官为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指挥控制而战,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鉴于他们对计算机、无线电、传感器和其他电子设备的依赖,冷战时期的专家们就回答了这一要求。他们的判断——即通过综合各种手段,包括物理破坏、行动安全、军事欺骗、电子战和其他手段,在指挥和控制方面存有的积极差别是必要的而且是可实现的——可以再次明确我们对信息行动的理解和方法。
声明:本文来自战例译注,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