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官网发布了该校教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梅杜舍夫斯基的文章《认知战争:社会控制、意识操控与全球主导工具》。文中指出,认知战争已成为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战争与和平议题辩论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认知战争究竟是全新形态的战争,还是仅作为混合战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信息、经济、政治领域与传统军事手段的融合?我们又应如何评估脑科学军事化对社会及政治合法性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全球资源、权力和影响力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文章剖析了认知战争概念的实质内涵、意识操控的技术体系,应对认知战争的策略及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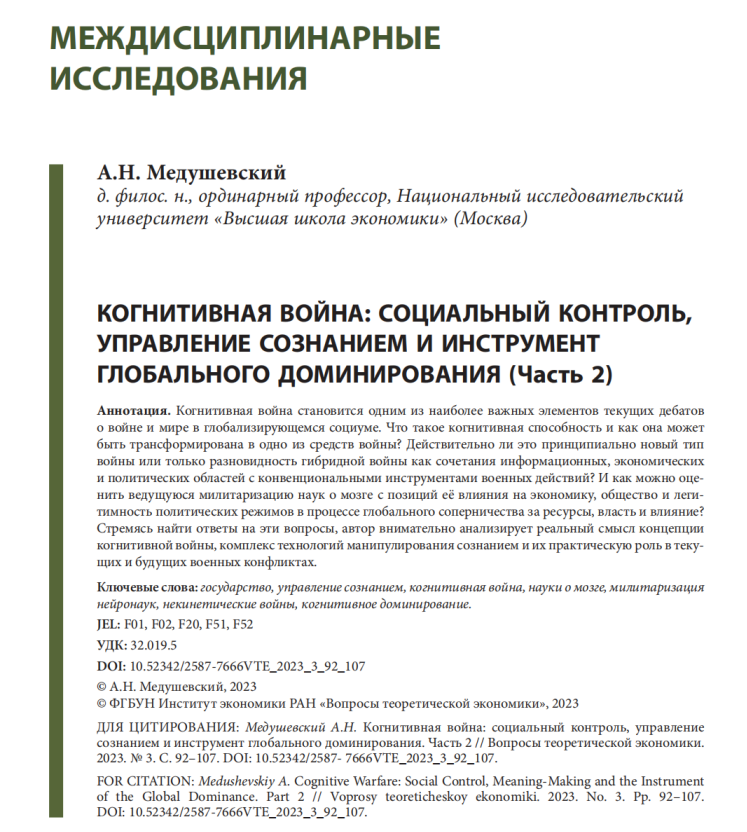
《认知战争:社会控制、意识操控与全球主导工具》
编译:和风
全文摘要与关键词
1.引言:21世纪的“脑战争”正逐渐成为优先方向,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法和国家法律的核心概念,以及社会控制、管理与战争实施的方式。
2.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认知战争:
①社会领域:认知战争的目标既可能狭义地集中于特定干预,也可能广义地指向社会的全面不稳定化;
②政治领域:认知战争主要针对通信基础设施和决策过程,其目标甚至可能是推动革命或政变。
3.认知战争的现代经验——趋势与实例:
①认知战争的变化趋势:规模扩大、西方国家未能完全实现认知战目标而其对手叙事在南方国家获得广泛传播、认知战争对民主国家越来越不利;
②认知战争的案例:西方国家策划的“颜色革命”,俄罗斯干预英国脱欧公投及美国总统选举;
③乌克兰的认知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认知战争策略效果不一。
4.如何应对认知战争:应对认知战争、信息操控和意识操纵技术的有效方法应是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认知模式,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进而引导新的认知活动。
5.认知战争的最终问题——能否取得胜利?
随着技术对意识控制能力的增强,战争的所有要素都会发生变化。然而,社会的认知适应能力、信息验证技术及创造性政治与军事精英的培养,可能成为限制认知战争影响的重要因素。总之,理想的认知战争胜利是可能的,但代价是所有各方都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然而,保持批判性判断能力仍然是战争与和平辩论中的关键要素,并且无疑是未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01
引 言
认知战争理论聚焦于通过新兴认知技术对意识进行操控。它勾勒了相关技术的范围并探讨了其军事化的可能途径。然而,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能够明确区分认知战争与信息战、网络战及心理战等概念。因为这些领域均涉及认知操控,并依赖技术手段(如信息压力、黑客攻击和网络战等)。因此,难以确定认知战争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立性:
• 与传统五大战争领域(陆地、海洋、空中、网络空间及太空)的关系;
• 所使用技术的特殊性(如针对神经网络的手段);
• 它究竟是军事对抗的革命,还是进化发展。
“脑战争”逐渐成为21世纪的优先方向。不过,毫无疑问,21世纪的“脑战争”正逐渐成为优先方向,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法和国家法律的核心概念,以及社会控制、管理与战争实施的方式。一些观点认为,应将认知战争视为一种国际法律框架内的战争罪,因为它对人类心理健康构成了威胁。然而,这种道德主张尽管合理,但显得过于理想化。在认知攻击已成为全球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显著改变战争的定义、法律框架及作战方式的背景下,单纯的和平主义呼吁显然不足。更具信息价值的做法是关注认知战争的参数,其成本与收益,以及对社会与政治体系的潜在影响。
02
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认知战争
社会领域:认知战争的目标集中于特定干预+指向社会的全面不稳定化
在社会领域,认知战争的目标既可能狭义地集中于特定干预(如外部势力干涉选举以助某一方胜出),也可能广义地指向社会的全面不稳定化(通过加强对立叙事)。认知操控的对象通常是负责解释社会现象和关键概念的社会群体,如社会国家、公有资源的归属权、对私有化的评价以及国家或民族爱国主义的解释者。
尽管民主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并未被取代,但其内涵因相互竞争的叙事而变得模糊。这些叙事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逐渐成为认知操控的工具。自由民主(保护少数群体权利)与非自由民主(保护集体权利)之间的矛盾,加之对民主真实性和民粹主义的不同解读,导致一些人提出“后民主时代”这一概念。后民主的特点在于,社会活动的意义被外部力量定义并强加给公众。
政治领域:认知战争主要针对通信基础设施和决策过程,目标可能是推动革命或政变
在政治领域,认知战争主要针对通信基础设施和决策过程(如选举与抗议),其目标甚至可能是推动革命或政变。在现代认知战争中,社会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影响通常是交织的,其核心目的是削弱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从认知战争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是一场关于“意义空间”分配的全球斗争,胜者能够取代原有国家的合法性,建立“植入型合法性”。
技术上,认知战争可以利用对国际法的操控。例如,在政治冲突中,各方对国际法规范进行完全不同的解读,以支持内部分裂或“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这种斗争不在乎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无论是传统主义者还是激进分子、民族主义者还是统一派——重要的只是其对目标政治体制的破坏性。
03
认知战争的现代经验:趋势与实例
完整意义上的认知战争可能更属于未来的范畴。然而,近年来,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认知战争的重要性,并在安全领域的文献中加入了对“脑部争夺战”的讨论。在全球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各方均分析了各自的优势与弱点。
3.1 认知战争的变化趋势
规模扩大:新冠疫情成为全球认知战争的新战场,各国指责对方应对不力,同时推广不同的危机解决策略,甚至互相指控对方人为制造危机或进行“疫苗战争”。
信息领域的失利与成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冲突中,尽管西方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未能完全使目标国家接受其叙事框架,被认为是认知战争中的失败。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对手在推广自身叙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并在非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
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威胁差异:认知战争对民主国家构成更大威胁,因为民主国家受到法律限制,而专制国家则更能自由利用民主国家的制度来推进自己的目标。
3.2 认知战争的案例
西方媒体经常提到的成功案例包括:
• 俄罗斯干预英国脱欧公投及美国总统选举;
• 借助疫情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
• 支持欧盟内部的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削弱欧洲一体化。
俄罗斯和中国指责西方在后苏联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策划“颜色革命”,并指出这些行动伴随着对相关事件的对立信息描述。例如,从新冠疫情到“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双方对事件的解读完全对立。
3.3 乌克兰的认知战争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认知战争策略效果不一。2014年通过“小绿人”(身穿无标记制服的俄罗斯士兵)占领克里米亚被视为成功的认知战案例,因为这场行动没有遭到明显的直接反击。然而,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西方通过有效的宣传战阻止了俄罗斯认知手段的发挥,成功地动员了乌克兰社会,最终导致冲突转向传统的军事行动。
04
如何应对认知战争?
摆脱认知对抗的恶性循环并非易事。简单的对抗认知战争技术可能无法奏效,因为这些技术会随着使用而不断改进,形成“无尽的升级”。为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认知模式,旨在通过批判性思维和信息验证来抵御认知战争的影响。
4.1 理解与解释:应对认知战争的方法
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认知模式。如何摆脱认知对抗的恶性循环?显然,不能仅仅通过用一种认知战争技术对抗另一种技术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些技术——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在应用中会不断得到改进,并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应对认知战争、信息操控和意识操纵技术的有效方法应是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认知模式,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进而引导新的认知活动。
这一替代性模型在奥尔加·梅杜舍夫斯卡娅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她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验证标准,并揭示了个体在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认知适应的形式。
4.2 信息交流:认知决策效率的影响因素
认知战争技术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认知适应水平,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在动态信息交换过程中作出决策的能力。真正信息的出现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而伪信息的产生则通常与个体的非活动状态有关。这种状态下,个体被动接收信息产品,成为操控的对象,导致疏离感和信息攻击行为的产生。
4.3 对抗认知战争的关键:信息质量与验证
然而,除了信息操控的过程之外,个体的自我认知能力(包括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批判性验证)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奥尔加·梅杜舍夫斯卡娅多次指出,信息技术已显著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些技术介入了个体与信息源之间。结果是信息资源量的急剧增长(例如大数据),但同时信息质量却大幅下降,因为这些数据缺乏必要的批判性验证,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操控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质量”成为关键问题。这不仅包括信息的真实性,还包括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可靠性和可用性。梅杜舍夫斯卡娅指出,必须在真正的和虚假的信息之间,以及伪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建立清晰的区分。
4.4 应对策略:批判性认知与创造性活动
历史经验表明,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应对信息操控和认知冲突:
• 外部统一目标的设定:通过外部刺激激发信息活动,例如通过防御性目标(修建“防御墙”)或理想社会构想(建立“人间天堂”)动员社会力量。这种方法是通过大规模的动员性活动人工创造信息动力,但它不涉及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反而可能增强认知战争的效果。
• 支持创造性状态: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创造性活动,将批判性认知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模式下,创造性的个体和精英群体通过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与被动接收信息的模式形成对抗。
05
认知战争的最终问题:能否取得胜利?
围绕认知战争的概念展开的争论,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社会政治对抗现实的重要变化。一方面,认知战争理论延续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即通过强加自身的世界观来争取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该理论聚焦于新的对抗对象——人类大脑与意识形成过程,以及实现全球主导地位的新技术和工具。
5.1 认知战争的局限性
对于认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人类思维的自主性:认知战争理论低估了人类大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将其简化为外部操控的工具;
• 对双方的模糊影响:认知战争对敌人和己方的意识都有影响,这模糊了战争的策略和战术目标;
• 无限持续的资源需求:认知战争需要持续动员大量资源,这种永久战争模式将导致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军事化;
• 社会分化与民主风险:认知战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以信息控制为标准形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这种控制强化了精英群体对信息的垄断,威胁民主传统。
5.2 传统战争的不可替代性
尽管认知战争引入了许多新特点,例如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模糊进攻与防御的界限,但它很难完全替代传统战争方式。认知战争可能通过刺激混合战争(例如“灰色地带”冲突)而促进传统战争的发展,而不是取而代之。
5.3 对认知战争的替代理解
与其使用“认知战争”这一术语,不如采用“现代战争中的认知维度”。随着技术对意识控制能力的增强,战争的所有要素都会发生变化。然而,社会的认知适应能力、信息验证技术及创造性政治与军事精英的培养,可能成为限制认知战争影响的重要因素。
总之,理想的认知战争胜利是可能的,但代价是所有各方都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然而,保持批判性判断能力仍然是战争与和平辩论中的关键要素,并且无疑是未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https://publications.hse.ru/en/articles/928889061
声明:本文来自认知认知,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